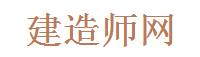那是2017年春天,我的《重回1937》创作到了尾声。应该是在寻访漆树坡窑洞保卫战过程中,从王照骞老师的讲述中听到武承周的故事,于是决定见见他。
“在他任武乡宾馆经理期间,有一天三次拒绝了一位日本客人的入住要求。”没错,就是他的故事吸引了我。这是怎样的一个人?身为宾馆经理,却要拒绝客人的入住要求?
武乡这片土地对日本人的仇恨,或许比别处更深一些。由西往东,从南到北,这里的山川、河流,都铭刻着日本人的诸多罪证。其中一条,就握在武承周手里。
武承周对日本人的仇恨,来自父亲。可是,他没有见过父亲,确切说是他的记忆里没有父亲。1943年6月,武承周出生于武乡县枣烟村。那一年,他的父亲武三林刚刚27岁,却已经是有着5年党龄的一名中共党员,在村中担任武委会主任兼治安主任。儿子的到来,让这个家更加完整。可是彼时,日本人在太行山中正猖獗,武乡那片土地也不例外。年轻的爸爸武三林也顾不得家里,更顾不得刚刚出生的儿子,与他的战友们日夜站岗、放哨,并跟随名扬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与敌人斗争。
这年农历六月二十一,武三林全家正在吃早饭时,驻村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12连连长刘玉兴急急忙忙跑来家里,告诉他有一支二百多人的日伪军已经从蟠龙出发,正沿着李峪及长乐村,一路烧杀抢掠过来,很快就会来到他们所在的枣烟村。武三林听罢立即放下碗筷,跟着刘玉兴开始转移全村百姓。
这个转移时间,还算充足。对于年轻且身手敏捷的他来说,更加从容,一村人都安全转移了。他随便往哪里一藏,便可以躲过这场劫难。可是偏偏,他没有停留在百姓避难的地方。或许是,他这个不穿军装的“战士”还惦记着村里其它事,总之将百姓安排妥当后,他又转身往村中折返。
武三林与剩余的另外5人,被带至另一个村庄。然而他并没有赢来获救的机会,反而遭叛徒出卖。敌人知道了他的身份,如获至宝,想从他嘴里探听关于八路军与游击队的信息。没想到,问,他不语;打断腿和胳膊,他不语;被刺刀捅,他依旧不语。敌人恼了,敌人怒了,疯狂地用锋利的刀在他的身上发泄……年轻的武三林,被活活折磨至死,身上留下28处刀伤。
接二连三的惨剧降临武家,摧垮武家人的身心,以致于他的母亲竭尽全力,生命还是终止在武承周8岁这年。
他没想到,在父亲惨遭杀害的53年之后,竟有日本人亲自找上门。和平年代,不能战斗,还不能拒绝吗?或者说,拒绝,就是一种无声的斗争!
彼时的相马一成不知道,尽管已经到了1996年,除了痛恨日本人,武承周心里还压着一块大大的心病,那就是当年到底是谁出卖了他的父亲。相马一成更不知道,英雄后人武承周一路走来,不仅未能因父亲的光荣牺牲得到关照,反而受尽屈辱。
武承周的父亲武三林,该是烈士。英勇献出生命两年后的1945年,他的名字也确实被铭刻在蟠龙镇奶奶凹山岗上的“抗日英雄纪念碑”上。然而全家没有想到的是,家中烈属待遇仅仅享受一年后,却被莫名取消。不仅如此,武三林还被说成是土改中被打死的,家庭成分也被定位成“上中农”。
灾祸突然降临,变化翻天覆地。武承周的人生注定要风雨飘摇。之后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,他因家庭成分备受磨难,严重时甚至想放弃生命。
可是,对父亲没有记忆的武承周,多方了解到父亲的死因,更相信父亲的人品,成年后便不断替父申冤。他当然也没想到,尽管事实明确,却始终难以翻案。
光明,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79年。这一年,他鼓起勇气拿起笔,给中央写信,给省里写信,最终在山西省民政厅的过问下,于1983年5月6日收到那张盖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”鲜红大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。
可是,他不敢松懈,也不能放心地喘口气,他的冤情还没有最终落定。那就是,当年到底是谁,狠心出卖了他的父亲——英雄武三林?当年到底是何原因,导致一夜之间父亲死因逆转,家庭成分改变?到底是谁的决定,把父亲的烈士名誉取消,家人的烈属待遇取消?
可怕的权力!可恶的人性!一个提不上桌面的狭隘的报复,就可以让英雄沉冤68年。而英雄之后武承周68年的漫漫长路,走的何其辛苦,何其悲壮!
今天,武承周已经整整80岁。他不再耿耿于怀当年的不公,更没有在解决了父亲与家庭问题之后停下脚步。他深知,武乡这片土地上,像父亲武三林一样的英雄还有无数。他们的名字,还在这片土地下尘封。他将有限的时间都用来了解这片土地,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。他曾真诚地对我说,“蒋殊,我年龄大了,这些资料都给你,希望你能把它写出来,传下去。“
上一篇: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下一篇:汽后独角兽倒闭:10年耗尽5亿CEO:努力到无能为力
- ·长江全长多少长江全长是多少
- ·关于布列瑟农铃声到底是什么原因?
- ·叫苦不迭(jiào kǔ bù dié)为什么上热
- ·有关入殓师工资是传言还是实锤?
- ·【投基方法论】光大保德信金昉毅:投资者
- ·有关毕业结业肄业真的还是假的?
- ·软银自作自受?外媒:投资方式为失利主因
- ·突勒是现在的什么地方突勒是现在的哪里
- ·枕(zhěn)戈(gē)待(dài)旦(dàn)到底是
- ·有关恋爱新手空间链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论
- ·国家统计局: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脱贫
- ·四川绵阳新增“4+5”其中8例在隔离管控人
- ·趣(qù)琅(lánɡ)庐(lú)赞(zàn)又是什
- ·关于波士顿法律第五季网友关心什么?
- ·华人健康: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顺利交易
- ·广东惠州市今宝山幼儿园组织积极参与疫情
- ·运动员入场词到底是什么情况?
- ·变与不变看两会——2020年两会记者观察
- ·关于风(fēng)鬟(huán)雨(yǔ)鬓(bìn)
- ·创识科技(300941)8月10日主力资金净买
- ·关于狙击手幽灵战士秘籍到底是个什么梗?
- ·关于闺房闹哄哄又是个什么梗?
- ·病有所医从“看上病”到“保健康”
- ·关于险(xiǎn)柳(liǔ)无(wú)是这样理解
- ·关于田单列传翻译到底是个什么梗?
- ·龙斗士焚天这件事可以这样解读吗?
- ·千(qiān)姿(zī)百(bǎi)态(tài)究竟怎
- ·关于武神新手卡背后的真相是什么?
- ·其中包括25只创业板新股和45只科创板新股
- ·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出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