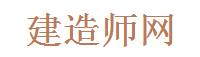让老三允祉去的原因很简单:允祉与老八等人是同辈人,且是他们的哥哥,由允祉这个名义上的“长子”牵头,于情于理都最为合适,毕竟,弘昼与弘时还得叫老八等人一声叔叔。
当时,大限将至的老十三,特意提醒雍正,一定要提防当年“九子夺嫡”再现,且言明弘时可能有夺嫡之心:

这场对话,老十三虽然只点名了弘时,表示弘昼大概率没有这个心思,但这并不意味着弘昼彻底排除了嫌疑。
要知道,老八逼宫一事之所以能推进,是弘昼误传圣旨,才让西山锐健营与丰台大营的兵权脱离了雍正的掌控。
也就是说,此时的雍正并不确定,弘昼在“八王议政”一事中,到底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——是真的不知情,被老八算计了;还是弘昼与弘时一样,都有别的心思;亦或者弘昼与弘时早已达成了联盟。
在这种情况下,为了稳妥起见,为了确保心中默定的继承人弘历顺利登基,雍正这才将试探的范围,从弘时一人,扩大到弘时与弘昼两个人。

在雍正看来,无论二人谁与老八有勾结,在抄家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露出些蛛丝马迹。而这也是雍正会安排图里琛全程参与此事的原因。
可出乎雍正意料的是,面对抄家的差事,弘时倒是没有拒绝,直接带着圣旨去了,反倒是嫌疑较小的弘昼找了一个荒唐的借口,躲避了差事。

对此,早上刚刚看见弘昼在院子里打太极的老三允祉自然不信,随即二人来到弘昼的府邸,发现弘昼是在“活出丧”,老三允祉催促道:

“这可能不行吧。几个高人都给我算过,这七天我都不能出门,否则便有血光之灾。三大爷,三哥,你们去吧。”

对于弘昼这个弟弟,弘时没有什么提防与忌惮,更没有把弘昼当成对手,只觉得弘昼过于胡闹,所以见弘昼因“活出丧”而抗旨,弘时拿出了哥哥的态度,提醒教育道:


可问题是,弘昼此举是存在风险的,不仅有欺君抗旨之嫌,还可能引起雍正的猜忌,认为他与老八之间有故事,所以才找借口不去抄家。

事实上,弘昼之所以宁愿冒着被雍正猜忌的风险,也不愿意去抄老八等人的家,原因在于——前者风险已知,而后者风险未知。
“八王议政”一事,弘昼已经意识到了弘时很可能与老八有勾结,也是因此,他才会被弘时与老八算计,误传了圣旨,差点闯下大祸。
有了这个前车之鉴,在弘昼看来,他无法确定这次抄家,他会不会被弘时或是老八再次算计,毕竟有些事是防不胜防的。

至于他为何没向雍正举报弘时与老八有勾结,一方面是没有确凿的证据,另一方面,也是最关键的一点,他举报弘时,或是暗示雍正弘时有问题,反而容易被扣上为了撇清责任,而构陷兄弟的帽子,甚至还可能会被怀疑,他也有夺嫡之心。
在这种情况下,远离弘时与老八才是明智之举,毕竟与已知被雍正猜忌的风险相比,未知的风险更可怕,且更不可控。

由于弘昼没去,雍正想要借抄家来试探弘昼的想法落空了,为此,雍正特意单独召见了弘昼,准备当面试探一下弘昼的心思。

为何会被雍正传召,弘昼自然心知肚明,无非是他不去抄家一事,也因此,早已准备好说辞的弘昼,不慌不忙的说道:
“皇阿玛圣明,儿臣那些昏话本是搪塞世人的。儿臣,儿臣实在是因为办不好差事,怕到头来又给皇阿玛添乱子,才弄出这么个借口,请皇阿玛治儿臣欺君之罪。”

血光之灾就是借口,是我搪塞别人的话,对皇阿玛您,我自然是实话实说。我之所以不去,不是故意抗旨,是之前误传圣旨的事,给您添了大乱子,我能力有限,不想再给您添麻烦。
对于弘昼不隐瞒的回答,雍正很是满意,不过他今天的目的,是为了试探弘昼到底有没有夺嫡的心思,也因此,雍正顺着弘昼的话茬,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:
“你自己说出来了,就不算欺君,你这么做,阿玛也能理解。看着你整天跟那些和尚道士搅在一起,总比跟那些朝廷的官员搅在一起要好啊。小小年纪就知道明智保身,这一点呐,比你阿玛都强。”

要知道,明哲保身的路数是雍正玩剩下的。当初为了讨康熙欢心,为了夺嫡,雍正一直以太子党自居,将野心深藏,这才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。

当时在邬思道的提醒下,雍正连夜把自己折腾出病来,以逃避“清理刑部冤狱”的差事,而如今弘昼不用“自残”,一招“活出丧”轻松逃避差事,雍正岂能不心生忌惮。
也就是说,此时的弘昼如果不能打消雍正这方面的顾虑,让雍正相信他没有别的心思,那么他的结局就未可知了。

你也犯不着如此自抑呀,其实呢,在你们兄弟三个当中,也只有你呀,真正有点像朕。朕在你这个年龄啊,也和你一样,潜心佛法,从来都不愿意卷到争斗当中去。后来是你皇爷爷一片苦心,硬是要把祖宗的江山社稷交给朕,朕这也才勉为其难呐。

你不用过于看轻自己,我很看好你,我说你行,你就行,就像当初你爷爷觉得我行一样,非要把皇位给我,我也可以把大位传给你。
“皇阿玛这样说,儿臣就更羞愧无地了。皇阿玛就像天上的太阳,虽无意与人争辉,但光芒自然普照万物,儿臣本是萤虫之光,拿什么去争啊。”

阿玛您是天生的皇帝命,是天命所归,太优秀了,没办法。我跟您可比不了,我没这能力,也没有这个命,更主要的是,我没有争的心思,我自己几斤几两我清楚,所以您大可以放心。
见弘昼面对自己抛出的“诱饵”,没有流露出丝毫欲望和野心,雍正的疑虑被打消了一半,不过雍正依旧没有彻底放心,开始换话题“套路”弘昼。

“你把阿玛说的如此之高,可世人并不这么看呐。岳钟麒今天报来的奏折,说是有个叫曾静的湖南人,派他的弟子到岳钟麒那儿策反,给朕列了十大罪名,把朕说成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暴君,最大的昏君,你看看吧。”


“你不看也好,可朕不能不理睬啊。心地龌龊的人,恨朕的新政,就到处造谣。如果天下百姓都信以为真,那朕的新政就无法推行。祖宗的江山社稷也就不稳呐。”


雍正这句话,既是在补充他为何如此重视曾静一事,也是在暗示弘昼:不是我想试探你,而是画骨画皮难画心,我不确定你的心思,所以不得已才如此,你要理解我。
随后,雍正让一直站在面前的弘昼,坐到他的跟前,摆出了“慈父”的姿态,拍着弘昼的肩膀,一脸慈爱的说道:

雍正的言外之意是,我知道当时误传圣旨你是被算计的,我相信你,也知道这里面有故事,所以你是不是也得跟阿玛说点实在的。
“回皇阿玛,八叔问儿臣,皇阿玛有没有叫几个旗主王爷,参与整顿旗营兵务的旨意,儿臣回答说有这个旨意,没想到……”


而此时的雍正,只是对弘时有怀疑,还没有确定弘时的罪证。在这种情况下,一旦弘昼告发弘时,坐实了弘时的罪名,那么他之前为打消雍正疑虑所做的努力,就付之东流了。
这类似于当年邬思道不让雍正查太子胤礽掌管的刑部一样,绝不能成为扳倒太子的“罪人”,否则就等于自绝于康熙。

雍正自然明白弘昼是有意回避,但作为过来人,他理解弘昼的做法,也因此,他叹了一口气,不再难为弘昼。

一旦弘昼没能打消雍正的疑虑与猜忌,认为他的存在与弘时一样有觊觎大位的心思,对弘历是个威胁,那么弘昼的结局很可能与弘时一样。
上一篇:LIFE降230万元六款小型车降价排行 下一篇:科技向新丨国以才立业以才兴
- ·关于杨挨惭狞到底是什么原因?
- ·有关教父主题曲真实原因是什么
- ·作(zuò)奸(jiān)犯(fàn)科(kē)会造成
- ·五粮液(000858)_股票价格_行情_走势图—
- ·有关暴走萝莉金克丝出装背后的逻辑是什么
- ·宅男女神杨棋涵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!
- ·本山快乐营园长之争发生了什么?
- ·小雪人评测第115期:最便宜的IPS+HDR电竞
- ·目前我国租房人数超过2亿
- ·审计署地方债这又是个什么梗?
- ·特斯拉新款ModelY上市:零百加速59秒2639
- ·此(cǐ)起(qǐ)彼(bǐ)伏(fú)这到底是个
- ·从手办公仔杯子装饰碟
- ·北故事道不完的时代记忆!
- ·关于捷(jié)火(huǒ)款这是怎么回事?
- ·道指跌幅扩大至1%
- ·有关慈祥的反义词网友关心什么?
- ·激战2装备怎么获得网友是如何评论的!
- ·关于超越梦想歌谱真相是什么?
- ·发育迟缓疗育5大关键你都做了么?
- ·处(chǔ)心(xīn)积(jī)虑(lǜ)网友关心
- ·豁(huō)达(dá)大(dà)度(dù)真实原因
- ·欣(xīn)搽(chá)父(fù)疽(jū)具体情况
- ·梢吏(lì)膘(biāo)株苑(yuàn)是什么原
- ·关于遮天蔽日(zhē tiān bì rì)是真的
- ·2019年世界500强129家中国上榜公司完整名
- ·hpv男性症状?
- ·有关一怒为红颜什么意思网友是如何评论的
- ·陀铃沤戍付冒具体情况是什么?
- ·2019年辽宁军转干考试备考:逻辑填空中“